本校董事長應《環球科學》雜誌邀約
撰文陳述對科學教育的觀點
刊登於2012年9月號雜誌內容全文
|
|
【環球科學雜誌封面】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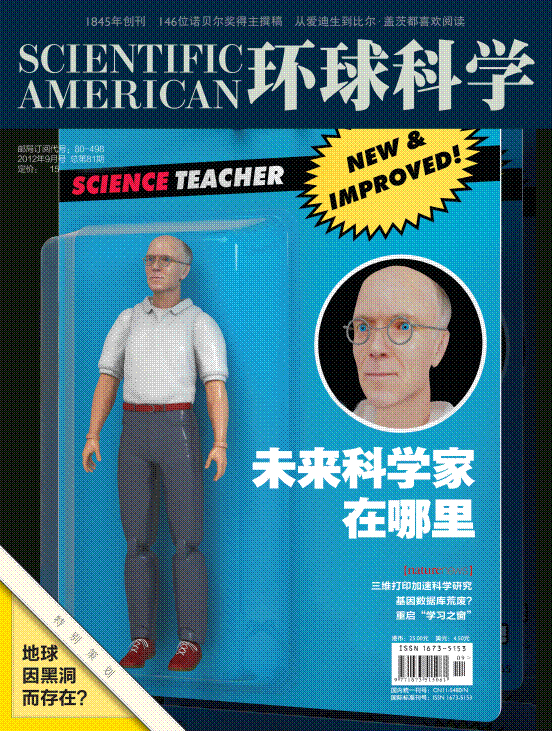 |
|
|
找准科學教育的重點
|
|
改變科學教育的方法,我們才能培育出更多影響世界的科學創新人才。
本刊記者 廖紅豔
|
|
楊定一博士是一位頗具傳奇色彩的科學家。
他6歲隨父親移民巴西,13歲以巴西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巴西大學,17歲隻身前往洛克菲勒大學,27歲任該校分子免疫及細胞生物學系主任。迄今,楊定一已發表了300多篇重要研究報告,碩果累累(參見《環球科學》2010年第2期《楊定一:從科學家到教育家》)。
但現在,他的科學家身份有所轉變——不僅是臺灣地區三所大學的校董,還參與大陸多所明德小學軟硬體規劃,致力於培養優秀的下一代科學人才。當過科學家,又投身教育事業的楊定一博士,或許能為科學教育這個重大問題提供一些借鑒。
|
| 《環球科學》:在臺灣地區,科學教育的情況怎麼樣? |
楊定一:臺灣中小學校內的科學教育算是有相當好的成效,比如,國際數學及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(TIMSS)結果顯示,臺灣學生的數學及科學測驗成績,在參加調查的40個國家或地區的50萬名學生中都名列前茅。此外,我們的學生參與各種國際科學奧林匹克競賽時也表現傑出,金牌、銀牌不斷。
相比而言,美國一向在TIMSS中表現一般,位列中游。美國主持TIMSS的教育學者指出,華人之所以在這些競賽中表現優秀,有兩個原因:一是專業優秀的師資,而美國中小學教自然科學的老師多數在大學時並非主修理科;二是課程結構,美國大多數中小學裏的科學課程,雖然教學課時數多且內容豐富,但缺乏合理結構。從一年級到九年級的課程裏,相同概念常常重複出現(如能量),結果是教得多卻深度不夠。而華人地區的學校科學課程結構嚴謹,循序漸進。
不過雖然臺灣學生在TIMSS表現優異,但其實臺灣與美國的教育制度各具特色與強項。美國講究方法論(Methodology)與邏輯推論(Reasoning),重視學生獨立思考能力而非知識背誦。臺灣強調大量吸收資訊與學識涵養,科學課程結構嚴謹,有時卻忽略了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。 |
| 《環球科學》:有沒有一種兼具“不讓一個學生掉隊”而又嚴謹的科學教育體系? |
楊定一:我個人認為科學教育的重點不在記憶背誦,而在邏輯思考能力的培育。這種改變很難借由一兩項措施就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,實在需要主政者及教育者從業者繼續深入地研究並改善。
在臺灣,九年一貫課程的基本精神是要脫離以前統一進度、統一標準的課程,實施教師與學校本位課程、以學生為中心的探究式教學,從而達到個性化、適性化的目標。但到目前為止,小學教育比較能做到上述的方向,但初中階段則困難重重,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學生創造能力的發展。
另外,臺灣的學校教育普遍為升學考試而準備,以致學習多為片段性知識,缺乏過程技能、基本原理教育,使知識與日常生活脫節。學校的學習非常功利,為了考試為了升學,這樣的小孩不容易培養學習的興趣。真正的學習興趣不是這樣來的。過度的課業壓力容易讓學生為了文憑學習,反而僵化了思考與創造的能力。 |
| 《環球科學》:那麼你認為該如何啟發學生的科學興趣、熱情? |
楊定一:這實在是太重要、太關鍵的問題。對科學的興趣不應是在大學或研究所才被鼓勵,科學家的養成計畫是長期且多層次的,在兒童時期就應著手培養。這也是為何在規劃為貧窮地區所設立的數千所明德小學時,我們建議要有多元化的科學課程、科學展覽與科學競賽的原因。
讓師長們採用正向鼓勵(positive reinforcement)的方式,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點燃學生對科學的熱情。不論是科學、音樂、文學或藝術,唯有鼓勵學生快樂地結合熱情與天賦,他們才能在熱愛的事物上發揮最大潛能,並找到人生的一條路。
現今的教育方法需要有所改變,不應該用分數或名次來量化學生的資質。教育者應採用活潑多元化的互動來啟發學生,讓科學融入生活與人生態度,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。唯有如此,我們才能培育出影響世界的科學創新人才,我們也能驕傲地說,華人在科學舞臺上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。 |
| 《環球科學》: 我們知道,你出生於臺灣地區,成長于巴西,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,你的成長、求學、工作足跡遍及各大洲。你認為從全球的角度來看,科學教育的重點是什麼? |
楊定一:不論中國大陸、臺灣地區,還是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的科學教育,現階段應著重“質”的精進,而非“量”的擴展。
從上世紀80年代始,各個國家和地區都積極培育科研人才,以推動高等教育的方式成功提升了科研工作者的數量,在人才數量上奠定了良好基礎。但如何提升科研工作者的素養與競爭力,則成為現階段最重要的課題。
比如,在“量”的方面,臺灣地小且人口不多,卻有164所大學院校(一般大學73所,技專院校91所)。每年約有31萬畢業生離開校園,其中科學相關領域(理、工、醫、農)約14.8萬人,但科技人才職缺卻僅約8.3萬個,明顯看出人才供過於求。也唯有“質”的提升,才能增加科技人才的競爭優勢。
所以,我們的科學教育也應重點著力於此。 |
| 《環球科學》:對於那些有潛力的年輕科學家,你認為他們最需要的發展條件是什麼? |
楊定一:我曾經歷研究生、博士後研究人員、教授、系主任等不同階段,也參與兩岸科學精英培訓與教育規劃。對於科學家的培養,我個人認為洛克菲勒大學的教育模式值得借鑒。
洛克菲勒大學的文化傳統是鼓勵有沖勁的年輕科學家,他們對科學的未來會有更為深遠的影響,這也是洛克菲勒大學能培育如此多諾貝爾獎得主的原因。
洛克菲勒大學有“科學麥加”(Mecca of Science)之稱,僅設立博士班,並無大學部或碩士班,每年招收不超過20名學生。大學以主題實驗室取代傳統系所,每個實驗室都為科學家提供獨立的協作空間。當時不論是我領導的“分子免疫與細胞生物學實驗室”,或其他不同主題的實驗室,其規模都遠超過一般學校的傳統院系,甚至組織架構更為多元化。各實驗室開展的大型主題研究計畫,研究內容不僅跨科系,甚至跨領域。這也就是所謂的“群聚效應”(critical mass),借由群聚的力量發揮科學研究的最高經濟效益,才能真正在科學領域有所突破。
我的老師梅裏菲爾德博士(Dr. R. Bruce Merrifield),因發明固相多肽合成法(solid state synthesis)對發展新藥物和遺傳工程貢獻良多,於1984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。梅裏菲爾德博士曾與我聊到,在他還是個研究剛起步的年輕學者時,曾有三年未發表任何論文,幸好當時洛克菲勒大學的校長與同事肯定他的能力,鼓勵支持他的研究計畫。事後證明,人才是效益最大的投資,而遠見也使得校長與同事成為化學發展史上的大功臣。
總之,一方面我們要給年輕的研究人員提供世界一流的科研平臺,另一方面要善於發現人才,對那些暫時沒有出成果的年輕科學家充滿信心,無條件地支持。我想這是他們最需要的。 |
| 《環球科學》:你目前也是臺灣地區三所大學的校董,能否談談在培養尖端科學家方面,你自己是怎麼做的? |
楊定一:有件事情很有意思,過去在《科學》(Science)和《自然》(Nature)期刊上有許多辯論,中心問題是,科學研究的規模究竟是“Big is beautiful”(大些好)還是“Small is more beautiful”(小些好)?其實我認為“Both are beautiful”(都不錯)。
多年來,我在臺灣長庚醫療體系、長庚大學、長庚科技大學都相當重視研究人才的培育。剛剛起步的科學家研究規模較小,處於個人自主且“Small is beautiful”的階段。在他們的研究初期,也就是最需要經費支援的時候,我們會助其一臂之力。
等到這些科學家的研究稍有起色後,他們再與其他資深科學家競爭相關機構的經費支援,進而擴大研究規模,進入“Big is beautiful”的階段。
在亞洲,經費支持往往傾向有經驗、有成就的著名科學家,其實這樣的科學家往往擁有相對豐富的資源與設備,不像年輕科學家易面臨經費上的窘困。
當科學家在一個領域獲得重大突破時,研究腳步一定要加速且重效率,如果關鍵時刻不能獲得協助,年輕科學家很可能就此功虧一簣,也可能造成科學界的重大損失。 |
| 》連結至簡體版原文(PDF檔) |